《2001太空漫游》上映50周年:伟大的人类进化畅想曲
时间:2018-06-20 来源: 澎湃新闻 作者: 澎湃新闻
为纪念已故大师——斯坦利·库布里克经典之作《2001太空漫游》上映50周年,第71届戛纳电影节组委会于今年五月电影节期间举办了特殊展映,放映影片70mm原版胶片全新版。克里斯托弗·诺兰首次出席戛纳电影节,负责此次电影的重映,并在电影节开设大师班分享库布里克对其电影事业的影响。2018年6月16日开始的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该片列入SIFF经典单元栏目放映片单中,于6月22日-25日放映《2001太空漫游》4K修复版。
作为斯坦利·库布里克“未来三部曲”之一的《2001太空漫游》上映于1968年,已跨越整整半个世纪。这部经典之作在上映之时遭人不解饱受争议,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受人顶礼膜拜。在1960年代末,它预言了未来世界的奇妙及其危机,并于50年后的今天,继续着它的预言。
“查拉图斯特拉凝视众人,感到奇怪。他如是说道
人是一根绳索,连接在动物和超人之间一一绳索悬于深渊上方。
越过去是危险的。在中途后顾、发抖和站立不动都是危险的。
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是一座桥梁,而非目的。人之所以可爱,是因为他是一种过渡,一种毁灭。“
——尼采 《查拉图斯特如是说》

《2001太空漫游》剧照。
作为斯坦利·库布里克“未来三部曲”之一的《2001: A Space Odyssey》上映于1968年,已跨越整整半个世纪。人们习惯称之为《2001太空漫游》,想来是因为更顺口且通俗易懂,但直译而得的《2001:一次太空奥德赛》却更为点题。《奥德赛》——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创作的长篇史诗,讲述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罗马神话中称为“尤利西斯”)在长达十年特洛伊战争结束后,继续漂泊十年才得以返乡的故事。《奥德赛》成为了西方经典表述样式。后代大量作家及哲学家以奥德修斯的漂泊和由此产生的对自我有限性的认知以及对不可逆转的过往时空的乡愁为原型,不断论述整个人类无家可归的精神漂泊。而电影《2001太空漫游》却并不对起源带有乡愁,它不夹杂忧伤地探讨人类的存在,继承尼采的永恒复归(The eternal recurrence)思想,用影像谱写另一曲《奥德赛》。
被压缩的角色:人类中心论的粉碎与永恒复归
伟大的哲思科幻片,不只《2001太空漫游》,还有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与《飞向太空》。在气质的庄严与思想的深邃方面,两位导演不分伯仲。而在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上,两位电影大师有着巨大差异。《2001太空漫游》以旷阔的时间跨度彰显其野心:一部概括人类过去、猜想人类未来的进化史,一部上映于1968年而2018年的我们依然处于其“猜想”部分前段的超验畅想曲。而塔氏科幻电影中所弥漫的形而上宗教气质及其深入个体的角度与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大相径庭。尤其是《潜行者》,其故事套用圣经中欲拯救人类的耶稣和双眼被蒙蔽的两位门徒之间的故事,借科幻讨论信仰的缺席,噬人的虚无主义与理性主义,以及女性诚挚而充满母性的爱情最终带来的奇迹。其人物的宗教价值观是影片推进的力量,绵延不绝的自白或和对白是影片的核心之一,整部影片便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外在化。
反观《2001太空漫游》:演员在这部影片中达到了布列松电影中的“模特效应”——角色被导演加以最大化压缩,成为影片的一个元素,而非人物。布列松称他的电影演员为“模特”(Model),他曾在《电影书写札记》中这样写道:“电影书写之影片,其影像如同字典上的字,离开了它们的位置与关系便没有能力和价值。”布列松的“模特”们在行动中成为电影书写的字,他们被禁止像戏剧演员那样进行表演,如棋子般被精心安排在电影中,互相碰撞。库布里克在《2001太空漫游》中类似的压缩手法被电影评论家宝琳·凯尔(Pauline Kael)所厌恶:"我们(观众)对于角色们的生死兴趣缺缺,我绝不感到意外。库布里克将角色们描写得如此乏味,部份原因是那些小人物和个人的宿命可能不够重要,不重要到一个程度,令某些重要的大导演不会垂下头关心。"
为什么一部关注人类进化史及未来命运的史诗级作品却将其中人类的角色压缩到“乏味”的程度?角色的复杂性不复存在,甚至是无性格。以至于没有观众能够对弗兰克和其他三位在人工冬眠中无声死去的博士代入情感,产生普遍意义上电影所能激发的移情作用?
答案其实很明了,影片的主题曲《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作品30》(Also Sprach Zarathustra,Op.30)就是答案本身:该曲是理查·斯特劳斯从尼采的同名著作中获取灵感而作。在《查拉图斯特如是说》第四卷第73节中,尼采声称:“上帝已死:现在我们希望的是——超人降生。”人是应该被超越的东西,超越他的便是超人(overman)。而超人论的前提便是上帝的缺席,有史以来基督教带来的人类中心论光环因此遭到了彻底的粉碎。影片中弥漫的对于人类角色的冷感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尼采的超人论,这种冷感是库布里克所选视角的必然结果——跳脱出人类群体,摆脱习以为常的自恋,以无限接近绝对理性的态度俯瞰宇宙,以此更为大胆和犀利地思考人类的境遇和未来。又有什么比着力突出这种冷感更能体现人类在浩瀚宇宙中十足渺小这一事实?又有什么会比这种冷感更能,十分矛盾地,体现库布里克对人类的关怀?
在影片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与这种冷感“相悖”的有趣细节:影片中唯一能够激发观众代入感的是人工智能电脑HAL 9000。在被戴夫关闭之前,HAL 9000表达出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它“临终前”哼唱着自己“出生之时”学会的儿歌《雏菊》,这一幕多多少少能够触发观众的某种情感。在整部影片的冷峻氛围中,HAL 9000的“死亡”被处理得稍带些格格不入的温度。关于HAL 9000求饶的真实原因也非常模糊:没有人确定这是因为人工智能进化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超级生物后产生的自然反应,或是这也只是人类为它输入的“拟人”指令之一(要知道,当下的日常生活中,让软件在删除前做最后一次求饶的指令已经非常常见)。但这一桥段至少提供了一种阐释的可能性,或是留给观众这样一种印象:人工智能产生了心智,也许会成功碾压自然智能,政权也许将得以交替。在我看来,对于HAL 9000“人性”一面的细密刻画的真实目的,在于着重表现“进化/超越”这一主题,而非迎合通常意义上的塑造复杂立体戏剧化的角色这一规则。

《2001太空漫游》剧照。
原始时代的猩猩(Moon-Watcher)在第一次触摸黑石后,开窍懂得运用骨棒来猎取食物。通过巧妙的蒙太奇,库布里克将猩猩手中的骨棒、人类的空间站、代表文明的笔串联起来,述说着从原始时代直至太空时代,人类强烈依赖自身所创造之物这一从未改变的事实。主题曲《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先后两次响起,为动物-人类-星孩(超人)这一进化史的转折点添加明确的标注。当我们看到作为人类的大卫战胜了HAL 9000这一具有高超逻辑、能够鉴赏艺术、似乎开启了心智的人工智能,后者终为前者所奴役时,可以注意到的是:库布里克对于HAL 9000的“死亡”进行了缓慢而细致的拍摄,其“死亡过程”更像是一段与整部影片的进化史主题相呼应的回溯过程:HAL 9000最终回归到自己的“童年”,唱起创造者教它的第一首儿歌,我们可以把这看作对于戴夫遇到神秘黑石迅速衰老后成为星孩(Star Child)的某种暗示。自然智能抑或人工智能,其生命轨迹化作一个能够让我们想到尼采口中的永恒复归的圈,只不过在影片中的永恒复归呈上升趋势,得以让人类进化为摆脱所有物质(包括肉身)的能量体,并等待着下一次轮回。
影像与声音:电影书写之作带来新的感受
罗伯特·布列松曾将影片分为两类: 使用戏剧手法(演员、场面调度等)和摄影机进行复制的影片;使用电影书写手法和摄影机进行创造的影片。”不同于“电影”(CINEMA),“电影书写(CINÉMATOGRAPHE)”是一种用运动画面和声音构成的写作。我们完全可以将《2001太空漫游》视为布列松所说的“电影书写”的完美样本。称此片为电影界的《纳尔齐斯和哥尔德蒙》并不为过:即理性与艺术的双重巅峰。
库布里克并非试图刺激而是要触动观众的感官,让其缓缓散发出想象力并从中生出思索,以取代廉价短暂的快感。当我们初到外太空,目光必然会缓慢而深重地被眼前的景象吸入,而太空重力的缺失及其浩瀚无垠也确实将给予我们一种深海游弋之感。这种特别的质感,通过光滑优雅的镜头来传达,也通过更为抽象的音乐——一曲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加以渲染,将观众置于这恢弘又轻盈的未来幻觉之中,实现文字所不能及的浸入效果。库布里克对速度及节奏的精准把握赋予画面以现实可感的瞬间,开片长达5分50秒(19:53 - 25:43)对外太空的描绘,不能不说是音乐和画面的完美结合。
在这部巅峰之作中,库布里克对于声音的把控极为精准。这里的声音确指:音乐、一切噪音、角色台词、人类的呼吸声等。我们在前面已提及到音乐所具有的功能:营造氛围、扩大空间、贯穿主题,同时也会注意到当骨棒被太空飞船以简洁快速的剪切加以替换之时,古典乐——人类音乐高级形式对猿人杂乱的吼叫声的替代。影片中的声音和画面之间的关系值得细说,以此探讨影片的美学及其带来的新的感受力。
影片在交代木星登陆任务的缘由桥段处出现了连贯和集中的台词,除此之外,台词的分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观众可以依靠导演简洁精确的镜头语言看懂这个故事(如果非要在影片中寻找缺陷,那么就是HAL 9000对大卫说出的“但是我会读唇语。”这句话实属多余)。在这样一部论述人类有限性与宇宙无限性的影片,词语——作为有限人类生命回应有限人类需要的产物”的确不应频繁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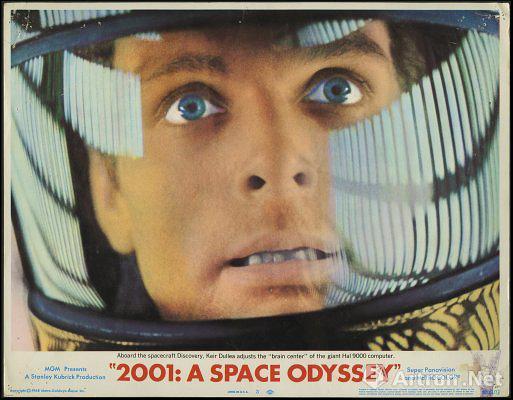
《2001太空漫游》海报。
而影片中人类的呼吸声比台词更为重要,尤其在某些镜头无法独自完成的桥段中:例如那一段令多数影迷匪夷所思的戴夫迅速衰老的过程。当戴夫战胜人工智能HAL 9000后,随即遇到黑石,随后进入星门,最终来到一间神秘的房间。在这间房间里,他迅速过完此生,临终前在黑石的伴随下,重生为星孩。在戴夫衰老的过程中,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视角切换。当年轻的戴夫抵达神秘房间时,在一片寂静之中,我们只能听到他在宇航服头盔内深重的呼吸,此时,观众与戴夫分享着第一视角并一道看到了对面离开了飞行器的另一个戴夫,此时的呼吸声依然深重,但是我们能够透过宇航头盔看到这另一个戴夫脸上有明显衰老的痕迹。当镜头再次切换为第一视角之时,我们再一次与衰老了的戴夫看到了更为年老的他,在后者扭身回望时,呼吸声消失,这意味着我们分享其视角的那个宇航员戴夫彻底消失了。接着,在第三视角镜头下,我们看到了年老的已摆脱了宇航服的戴夫循着另一种深重的呼吸声,看到了处于弥留之际的自己。呼吸声作为唯一的声音,是标注不同阶段里戴夫消失的精准坐标。依据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推断,当观众与戴夫看到摆脱飞行器的另一个他时,飞行器内的戴夫即时消失,呼吸声之所以没有随之消散,是因为前后两阶段的戴夫依然身着宇航服。
有趣的是,随着不断的衰老,戴夫不断进化,飞行器、宇航服、重力(神秘房间的失重状态似乎一目了然的,房间的布置像极了神秘生物对于地球日常的拙劣模仿,其诡异的氛围更是令人想起今敏动画《她的回忆》中所呈现的太空城堡)先后为他所弃,一步步消解人类从原始时代(骨棒)至太空时代(人工智能)对工具的依赖,回到永恒复归的最初点,正如归家的奥德修斯。
戴夫在神秘房间里不断看到自己,似乎来源于黑石的神秘力量。从空间的纬度去看,这正如博尔赫斯笔下的“我”在隐藏于卡洛斯·阿亨蒂诺那栋位于加拉伊街老家地下室里的阿莱夫中看到自己一样。它们是神秘的力量,是空间的一个包罗万象的点,从各个角度看到的、全世界各个地方所在的一点。一个无限的总体。从时间的角度看,法国哲学家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不正确认了在时间的长河中,布满了不同于当下自我的新的自我的产生与前者的消失吗,两者之间的相异性(Altérité)无法消弭。当然,遗憾的是,影像无法表达在这个神秘房间中时间碎片的水平性。
这部经典之作在上映之时遭人不解饱受争议,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受人顶礼膜拜。在1960年代末,它预言了未来世界的奇妙及其危机,并于50年后的今天,继续着它的预言。这部影片在令人的感官无限接近真实的同时又布满了符号与隐喻,让可感与哲思交织。《2001太空漫游》如同它所拍摄的那块具有9:4:1精密比例的黑石,保持着永恒肃穆的力量。至于随后受其启发与影响的多数科幻片,一部分成为了从古典乐中捞取片段编写而成的顺耳流行歌曲、从艺术品中获取灵感的大众文化产品;另一部分虽有着同样严肃的内核,却因其电影语言的平庸,削弱了影像和感觉力量。







